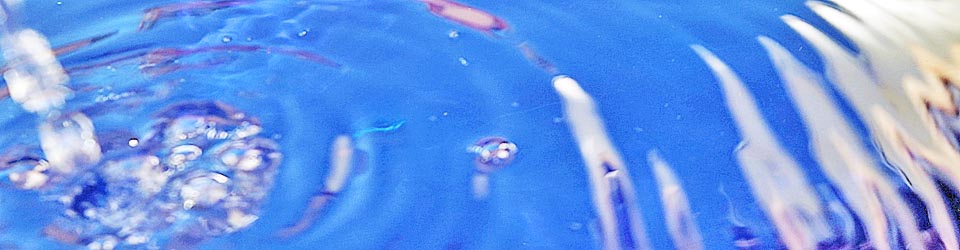Andreas Peglau[1]
(这是 DeepL 的自动翻译,未经我审核。对于其中肯定存在的错误,我深表歉意。)
自人类存在以来……
「战争是指有组织、使用大量武器和武力进行冲突,参与冲突的集体有计划地行动。参与冲突的集体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 为此而发生的暴力行为有针对性地攻击敌人的身体,导致死亡和受伤。」(维基百科)[2]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 520 年至公元前 460 年)曾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万物的父亲。」[3] 1642 年,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描述为原始的自然状态。 [4] 不到 300 年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引用了霍布斯的另一句话,声称:「人就是人的狼」,是一种「野兽,对同类毫无怜悯之心」,其根源在于「人类之间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敌意」。[5]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无需考虑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战争是在为谁的利益而打:这只是我们的基因使然……这还意味着:从长远来看,战争几乎无法避免。即使能够避免,也只能以压制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天性」为代价。
时至今日,战争是一种原始的、几乎「自然」的状态的论断仍然存在。以下两个例子:
2009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宣布,他比所有前任总统都承担了更多的战争责任:[6] 「战争以各种形式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7]
在趋势研究者马蒂亚斯·霍克斯(Matthias Horx)创立的「未来研究所」的网站上,2024 年写道:「自人类存在以来,战争就一直存在。」[8] 这里甚至认为自己非常清楚:
「最暴力的社会是——或者曾经是——那些我们通常认为」和平“的社会。狩猎和采集社会谋杀率最高,地球上大多数地区都发生过无休止的部落战争。在自然原始状态下,人们拿走能拿到的东西,其他部落的成员不被视为「自己人」,杀人的顾忌几乎不存在,特别是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 [9]
与这种「原始状态」相比,贫穷、剥削、压迫和战争被法律所规范,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当然显得像是一种纯粹的救赎。
回到远古时代
让我们来看看目前关于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于考古学证据稀少,人们往往依赖猜测和「类比推理」[10],而且专家们之间对大多数理论都存在争议,一个新的发现往往就会颠覆整个理论体系,因此以下一些信息,尤其是关于年代的,只是暂时的。我希望我由此得出的结论能够长期有效。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导致现代人类的物种与导致现代黑猩猩的物种分道扬镳是在大约六百万年前。[11]由此产生了最初看起来还比较像猴子的生物,也被称为「原人」。从这些生物演化而来的「原始人类」和「早期人类」是「人类」物种的最早代表,出现时间可追溯到两百万到三百万年前。[12] 迄今为止,已经证实「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即智人,存在了大约 30 万年。[13]
人们普遍认为,火的使用对人类进化过程做出了贡献。在「知识星球」网站上,我们了解到:[14]
「一些发现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 150 万年前就已经利用了火的力量。但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独立点燃火,这个问题在研究人员中仍然存在激烈争议。许多人认为,4 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借助火石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上述数字准确,那么我们的祖先在近 150 万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使用火,却从未发现如何自己生火。因此,其他科学家,如历史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将这个时间推得更早,大约在 40 万年前,也就不足为奇了。[15]
40万年还是4万年?在这36万年的巨大差异背后,隐藏着研究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根本问题:尽管我们对人类逐渐进化成人的漫长历史有许多猜测,但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却少之又少。
没有代表性的结论

在 2021 年出版的《起源:人类的新历史》一书中,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总结了当前的研究状况。他们写道:对于我们的早期史前历史,
「几乎没有任何发现。因此,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活动的唯一证据只有一颗牙齿或几块打碎的火石。[…]
这些原始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子?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诚实承认,我们完全不知道。[…]
对于大多数时期,我们甚至不知道人类喉头以下的结构,更不用说肤色、饮食等其他方面了。“[16]
2024 年,考古学家哈拉尔德·梅勒、历史学家凯·米歇尔和进化生物学家卡雷尔·范·斯海克证实:“我们所发现的人类骨骼数量少得可怜。」 [17] 他们引用的一项估计称,已发现 3000 具「超过 10000 年的智人遗骸」。[18]
截至当时,地球上曾居住过的原始人、远古人、早期人类和现代人的总数,有一个非常推测性的数字,超过 70 亿。[19]由于人类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增长缓慢,因此绝大多数人属于智人(Homo sapiens)群体。[20]
数十亿散落在地球一半以上的个体,只有几千具遗骸,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找到的遗骸越来越少:这表明,关于早期类人生物和人类的所有概括性结论都是多么站不住脚。少数个体的骨骼残骸根本无法代表大量活人的情况。
牙齿和颅骨占这些发现的大部分,但它们根本无法提供关于其前主人的心理和社会方面信息,包括他们是否好战或爱好和平。
而「我们今天所称的『文化』的最早直接证据」也「不超过 10 万年」。而且,直到不到 5 万年前,这样的证据才逐渐变得多起来。[21]
但那时智人已经存在至少 25 万年了。然而,除了最近五千年之外,我们认为自己了解的关于这 25 万年间人类的心理状态、动机、目标和社会行为,几乎完全基于或多或少合理的假设。
2023 年 6 月 6 日的一条新闻再次表明了这些假设的初步性:20 万年前,类人祖先就已经埋葬了他们的亲人。到目前为止,只有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被认为有这种行为,而且是在 10 万年前。该消息称,这些发现「挑战了人类进化迄今为止的理解,即只有大脑发育到一定程度,才能进行埋葬死者等复杂活动」。[22]
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汉内斯·斯图贝(Hannes Stubbe)在《世界心理学史》一书中对早期考古发现及其推断进行了简要汇总。[23]
照顾而不是谋杀
另一位人类学家布莱恩·弗格森(R. Brian Ferguson)在多个地点对数百具超过一万年的智人骨骼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它们是否受到过人际暴力伤害。只有大约三打骸骨存在这种情况。这意味着,他没有发现 10000 多年前发生过战争的考古证据。此外,暴力行为并不一定是有意的。[24]
事实上,在史前时代也有证据表明存在人际暴力行为,最早的可追溯到大约 43 万年前。 [25] 在《暴力进化》一书中,梅勒、米歇尔和范·斯海克对人类出现以来的整个三百万年进行了仔细研究,「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线索」,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甚至没有几例故意杀人的证据。」[26]
但即使这些杀戮是谋杀,由于缺乏目击证人,这一点永远无法确定:谋杀并不是战争。而且,一个谋杀者(与受害者相比,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能代表当时的人类群体。
哈拉尔德·梅勒和他的合著者还指出:
 「如果寻找史前战争、谋杀和杀人的证据,你会发现的是照顾和关怀的痕迹。古考古学发现证明:人类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否则许多伤势都会导致死亡。」
「如果寻找史前战争、谋杀和杀人的证据,你会发现的是照顾和关怀的痕迹。古考古学发现证明:人类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否则许多伤势都会导致死亡。」
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同样是在大约 43 万年前去世的一名尼安德特人,他“患有一系列退行性疾病、创伤、右臂缩短、左眼失明以及严重听力障碍 ,但仍然活到了「四五十岁」——只有在他每天得到群体包括伤口治疗在内的帮助的情况下,这才有可能。[27]
「战争」的标准
此外:并非所有故意的人际暴力行为,甚至并非所有使用武器的冲突都是战争。再次参考维基百科:
「对战争进行分类的一个基本难题是,何时才能将一场冲突称为战争。在政治和学术上,人们通常将武装冲突与战争区分开来。武装冲突是指交战各方之间偶发、偶然且无战略目的的武装冲突。“[28]
该词条还指出,「在大型研究项目中,每年死亡人数达到 1000 人被视为武装冲突升级为战争的粗略指标」。其他「战争定义」还要求「至少一方具有最低限度的持续规划和组织行动」,或者「至少一方是参与冲突的国家,并出动军队」。[29]
一个长期被认为是最古老战争证据的发现,最多只能部分满足上述标准。R. 布莱恩·弗格森(R. Brian Ferguson)报道了在今苏丹进行的发掘情况:
「这个被称为 117 号遗址的墓地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考古学家弗雷德·温德福领导的一个考察队发现的,据粗略估计,其历史可追溯到 12000 至 14000 年前。墓地中发现了 59 具保存完好的骸骨,其中 24 具与石块紧密相连,这些石块被认为是投射物的碎片。“[30]

目前,那里已经发现了 61 具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尸体;41 具骸骨上有伤痕。[31] 但无法确定这些死者是同时埋葬的,还是在几年时间内埋葬的。在《人类发明战争》一书中,史学家迪克·胡斯曼指出,弗雷德·温多夫「在附近发现了另一个同期的墓葬地」,那里「没有发现任何尸体有伤痕」。因此,人们认为,在 117 号遗址中,可能「只有那些死于非命的人被安葬在这里」。[32] 然而,现在事实证明:「许多人的尸体上有伤痕」,大多是箭或矛造成的,「这些伤痕在他们死亡时已经愈合」;[33] 四分之三的成年人都有这种情况。
因此,迪克·胡塞曼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可以「排除」大屠杀的可能性。[34] 然而,这些发现证明「人际暴力屡屡发生」。[35]
5888万年没有战争痕迹
但是,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具体情况,想把大约 12000 年前在苏丹发生的伤亡事件归类为战争,从人类出现 600 万年来看,这意味着 5988 万年(占 99.98%)的时间里没有战争的证据。如果我们以早期人类,即智人出现以来的 300 万年作为参考基准,那么在 99.96% 的时间里,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即使我们只以迄今为止已证实的智人存在 30 万年作为参考基准,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存在的 96% 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发生过任何战争。同样,在 45 万年前就作为「独立物种」存在的尼安德特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发生过战争。[36]
哈拉尔德·梅勒、凯·米歇尔和卡雷尔·范·斯海克也承认,在漫长的历史中,「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表明存在战争或群体之间偶尔发生的冲突」。考古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从人类历史来看,集体、有组织的屠杀似乎是一种新现象」。[37]

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瑞安和精神病学家卡西尔达·杰塔在他们的《性:真实的故事》一书中问道: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在一个肥沃、基本上无人居住[38]、资源丰富[39]的星球上,进行艰苦的迁徙,去杀戮其他人或被杀?与此相吻合的是,在目前已发现的数千幅史前洞穴壁画中,没有发现任何战争场景。[40]
大约在 7000 年前,出现了多个集体墓葬,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些墓葬是战争屠杀的证据。[41] 最早的图像描绘了弓箭手们似乎在对抗,[42]目前普遍认为这些图像的年龄约为 5000 年。[43]
可以推测,战争主要是专制社会结构形成、随之而来的财产分配不均的结果,也许还受到自然灾害及其各种影响的推动。[44]
到此为止,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巴拉克·奥巴马或未来研究所(「自人类存在以来,战争就一直存在」)在开头引用的句子完全无法证实,因此是不科学的。
然而,那些仍然传播此类言论的人必须问自己,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什么理由,出于什么动机。对于奥巴马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将战争视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可以减轻他发动战争时的良心负担。
同样,当今政府和媒体中的战争鼓吹者们也可能利用我们天生就具有破坏和杀戮的倾向甚至欲望,来让我们接受他们所追求的「战争能力」,其口号是:“你们本来就想要的!」
原则上来说,相信人类天生具有破坏性的人,就无需去思考是什么使人类变得「邪恶」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认识的局限性
当然,由于缺乏对人类早期历史进行客观评价的可能性,我们同样无法证明人类起源完全是和平的,也无法证明人类起源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共产主义或母系社会状态。1996 年,经过深入的研究,考古学家布里吉特·罗德、朱莉安·胡默尔和布里吉塔·昆茨得出结论,母系社会「无法通过考古资料来证明或反驳。考古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无法了解过去社会的思想世界」。[45]
在过去的 5 万年中,洞穴壁画和人物形象等(需要解释)为了解这种思想世界提供了线索。然而,只有当人们能够以持久的方式记录书面语言(例如楔形文字)时,更可靠的「钥匙」才得以发展,这大约是在 5000 年前。 [46] 即使这个钥匙也不是完全准确的,书面记录往往是不准确、歪曲的,而且几乎总是残缺不全的,这已经由一句有道理的话所证明: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著名的复活节岛事件中,征服者和奴隶贩子将他们自己对当地土著居民造成的破坏归咎于土著居民。[47]

在历史观中,对「原始」文化的诋毁屡见不鲜。例如,尼安德特人就被描述为「肌肉发达、智力低下、愚昧无知、毫无文化」的「外星人」,[48]尽管许多发现早已证明,这种大约在 4 万年前灭绝的人类与智人(Homo sapiens)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同, 同样「人性化」,并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繁殖与智人杂交。[49] 汉内斯·斯图贝指出:尽管一些科学家「难以承认这一点,但今天我们必须接受尼安德特人是具有所有智力、心理和社会功能、能力和技能的完整的人」。 [50] 而且,尼安德特人的大脑比我们的大……[51] 马丁·库肯堡(Martin Kuckenburg)在多篇出版物中为尼安德特人作为「第一位欧洲人」伸张了正义。[52]
关于「战争能力」的话题,还有两个扭曲现实的例子值得注意。只有通过一种已经详细揭露的粗暴数据操纵[53],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才能声称,过去「集体暴力……一直存在,无处不在」[54],并由此得出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想化结论。 [55] 人类学家拿破仑·查格农[56] 的做法尤为厚颜无耻,他先是在 1964 年向亚诺马米人赠送了斧头和砍刀,然后在畅销书中根据这些斧头和砍刀以及各种虚假陈述,声称他们非常暴力。1995 年,雅诺马米人因他持续的诽谤而禁止他进入他们的领地。[57]
但查格农和平克仍然被作为土著人民残暴和先天邪恶的首席证人。

历史学家鲁特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收集了「邪恶的野人」这一「标准叙述」的虚伪性的例子,这些野人只有通过「善良的」(西方)文明才能使其社会化,并批判性地审查了关于人类形象的所谓科学实验、研究和出版物。
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基本上是善良的」,这正是他书名的含义。[58]
上述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回答人类是否天生好战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人类天生具有战争和杀戮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就必须随时随地表现出来——即使只是因为这种倾向必须不断被压制。因此,要否定「人类天生就是战士」的说法,我们只需证明过去或现在存在不同的情况即可。就过去几千年而言,这完全有可能。[59]
狩猎和采集
关于我们的近亲祖先——他们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通常被称为「野猎人」——哈拉尔德·梅勒、凯·米歇尔和卡雷尔·范·斯海克认为,应该「埋葬托马斯·霍布斯[60]的偏见」,认为他们的生活「孤独、贫穷、恶心、野蛮且短暂」。 [61] 显然,他们比「当今的平均人」更高,克里斯托弗·瑞安和卡西尔达·杰塔认为,他们的预期寿命可能在 70 到 90 岁之间。人类学家罗伯特·埃杰顿也认为,在欧洲,「城市人口可能直到 19 世纪中期甚至 20 世纪才再次达到狩猎采集者的寿命」。[62] 这些游牧民族显然「非常适应他们的生活环境」,几乎没有因为资源缺乏而发生冲突的理由。[63]
人类学家道格拉斯·P·弗莱与哲学家帕特里克·索德伯格对 21 个过去和近现代的狩猎采集社区的「148 起致命侵略事件」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64] 他们将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这些死亡事件大多是出于个人动机,如嫉妒或报复,很少是家族仇杀,更「罕见」的是「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大约一半的群体中根本「没有涉及多个肇事者的致命事件」。[65]

狩猎采集制度并不是只存在在国家出现之前,而是与大约 6000 年前首次出现的国家一起存在了数千年。[66]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他的《文明之磨》(Die Mühlen der Zivilisation)[67]一书中所指出的,这种并存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狩猎采集生活仍然是一种比定居生活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在防御工事坚固的定居点,人们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最初并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原因之一是,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家畜的密切接触导致了传染病,而且人们现在被迫主要在一个地方获得生活必需品。
但在新兴的大城市中,也有和平共处的例子。其中一个定居点是安纳托利亚的卡塔尔胡耶克(或Çatalhöyük),[68]它从公元前7400年左右开始存在了大约1500年,面积达13公顷,有数千居民。食物和物质财富的分配似乎相当均匀,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中央秩序机构,更不用说压迫机构了,也没有暴力犯罪或杀戮战斗的迹象。
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 5% 的定居点被考古发掘出来。[69] 尽管如此,这仍然有力地表明战争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数。
通过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民族学研究,还可以证明,智人可以长期和平相处。
向最和平的社会学习
2021 年,长期研究和平维护机会的道格拉斯·P·弗莱[70]和社会心理学家彼得·T·科尔曼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他们的「可持续和平项目」(Sustaining Peace Project)[71]。自 2014 年以来,他们的团队由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环境学家、政治学家、信息与通信专家组成,致力于「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持久和平」。科尔曼和弗莱写道,与媒体通常的描述相反,迄今为止,仍有许多社会在其边界内以及与邻国「已经和平相处了 50、100 甚至数百年的时间」。这反驳了「人类天生就注定要战争」的信念。[72] 他们列举了巴西辛古河上游的十个邻近部落、瑞士各州以及易洛魁联盟等例子。

他们总结出以下几点对促进和平特别有利:一个更高级的共同身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集体活动和机构/反对战争的规范、价值观、仪式和象征/在大众媒体中使用「和平语言」(如果有的话)/政治家、企业家、神职人员和活动家,他们为发展和实现和平愿景做出了贡献。[73]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在今天的德国或欧盟,这些因素存在吗?科尔曼和弗莱也将欧盟归类为爱好和平的社会。但他们的文章还是 2021 年的……
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Sustaining Peace Project[74] 网站建议阅读弗莱的《人类和平潜力》(The Human Potential for Peace)一书(遗憾的是没有德语版本)。
人类破坏性的解剖学
早在 1973 年,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就整理了关于不同种族及其社会关系质量的报告。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人类破坏性的解剖》[75]中,他写道,在 20 世纪下半叶,仍然存在稳定、热爱生命、不好战、往往以母系为导向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没有必要抑制所谓的杀戮本能。[76]弗洛姆总结道:
「虽然我们在所有文化中都发现,人们通过战斗(或逃跑)来捍卫自己的生命,但在许多社会中,破坏性和残忍性却微乎其微,如果这是「与生俱来的」激情,那么这些巨大的差异就无法解释了。“[77]
据我所知,弗洛姆的书还提供了最全面的论据汇编,这些论据来自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心理学和历史学,支持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合作与和平倾向。
我只想简要地提一些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要点:
– 侵略本身源自拉丁语「aggredere」,意为「走向某人或某物,采取行动」,它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我们行为方式中必不可少、健康的一部分。只有借助它,我们才能划清界限、实现自我、维护和捍卫自己。在生命的开始,我们就需要这种能力来挤出狭窄的产道,来到这个世界。动物和人类都具备这种健康的侵略能力。它总是与威胁性的情况或挑战联系在一起。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提出的侵略本能甚至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死亡本能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78]
– 在某些情况下,侵略性行为也会伴随着破坏和毁灭,例如狮子捕杀羚羊,或者人在紧急自卫时杀人。但无论是动物还是心理健康的人,这种破坏绝不会成为目的本身。
– 动物和心理健康的人不会表现出虐待、蓄意杀生、残暴的行径。只有被摧毁、因此心理严重失常的人才会想要战争。
– 人类能够预先在头脑中想象出真实的或虚幻的、只是暗示性的生命威胁。后者也会引发人类生物性的、为了物种或自我保存而产生的侵略或破坏行为。权力精英们经常利用这一点来制造大众的战争准备。
– 有意义的生活、充实的人际关系以及深入的心理治疗都有助于减轻或治愈导致破坏性的社会化的影响。[79]
我们是否作为潜在的杀手来到这个世界,也可以通过个人履历来检验。那些犯下战争和种族灭绝等严重罪行的人,他们的生平就是最好的例证。
戈培尔
约瑟夫·戈培尔[80],生于 1897 年,后来成为纳粹宣传部长,是纳粹国家反犹太、反共产主义和反苏联战争宣传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戈培尔是一个狂热的人,他写诗、剧本和钢琴曲,阅读戈特弗里德·凯勒、西奥多·斯托姆、席勒和歌德等人的作品,坠入爱河,希望过上充满爱和认可的生活。他儿时患上的马蹄内翻畸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种残疾的负面反应,使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于他虔诚的天主教父母来说,这是一种「厄运」,最好是完全否认。他的亲戚和同学对他感到厌恶,甚至憎恶,后来一些他心仪的女性也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人未实现的爱情被「祖国」这个替代对象所取代。然而,1919 年,作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 22 岁青年,戈培尔成功地申请到一位犹太教授的博士学位,并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和「彬彬有礼的人」。 [81] 1920 年,他如此反思西德最初胜利的「左派」群众起义,反对反动的自由军团和帝国国防军:「鲁尔区的红色革命……我远在千里之外,却为之兴奋不已」。[82]
在寻找能够拯救自己和德国的「天才」的过程中,他于 1921 年第一次听说阿道夫·希特勒,并感到失望。他写道:「只要看到纳粹党徽,我就想拉屎。」[83]
然而,职业和私人生活的挫折、失业、饥饿、生存不安接踵而来,[84] 精神问题日益严重:感到生活毫无意义、产生自杀念头、酗酒、精神崩溃。此时,他「深度抑郁」与「狂热意志爆发」交替出现。[85]
1922 年,他得知未婚妻是「半犹太人」,虽然感到不安,但并未立即结束这段恋情。[86] 1924 年,他仍然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87]
但渐渐地,他完全沉迷于纳粹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让他压抑了自卑感和抑郁情绪。正如他所写的那样,现在,在他眼中,「天空中形成了一朵白云,形状像一个卐字」。[88] 希特勒的无条件追随者已经准备就绪。
然而,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 30 年。
希特勒

几乎没有人像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有如此多的出版物。2020 年,又有一本书出版,汇总了目前关于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知识:《希特勒——塑造他的岁月》。[89]
这再次表明:青春期的希特勒显然越来越受到自卑感的影响,并通过膨胀的野心来弥补;顽固、固执和言语攻击性也日益严重。然而,这并不奇怪,在当时对儿童和青少年部分残酷压迫的典型环境下,他也不例外。
而且,希特勒长期以来还保留着另一面,即情感上的波动性。犹太医生爱德华·布洛克曾努力挽救当时 18 岁的希特勒的母亲免于死于癌症,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几十年后,他描述了在希特勒母亲去世当天对希特勒的印象:
「阿道夫坐在母亲身边,脸上露出彻夜未眠的疲惫。为了记录下母亲的最后形象,他画了她[……]。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被悲痛摧毁的人。[…]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他会成为一切邪恶的化身。“[90]
因此,即使是戈培尔或希特勒,也不能说他们生来就是怪物,天生就具有「战争才能」。
此外,对士兵的研究有时也能给人带来希望。美国军事专家戴夫·格罗斯曼证明,「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克服士兵杀人的厌恶感」。只有通过「麻木的训练和有针对性的训练」,才能消除「杀人的心理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士兵对杀戮准备不足,「只有 15% 至 20% 的步兵开过枪」。[91]
要点
1)人类一直都在打仗的说法缺乏任何科学依据,是不严肃且具有误导性的。
2)我们是否是「天生的战士」,「战争能力」是否属于人类本性,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科学来研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有孩子或与幼儿有足够密切接触的人,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认为这些孩子毫无理由地具有攻击性甚至破坏性——是「天生的战士」,具有杀戮的倾向。现在,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都证明,我们出生时就具备亲社会行为、爱、友谊、合作与和平的潜能。[92]而这种潜能迫切地想要实现!即使是今天再次发动战争和大屠杀的政治家,甚至那些执行这些杀戮的人,几年前也都是作为好人来到这个世界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都具备在良好的社会中成为好人的所有必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人类早期历史进行合理的推测。许多科学家现在都接受这样一个论点,即所有智人(这里可以补充尼安德特人)都具有「心理统一性」。换句话说:自从「现代」人类出现以来,他们就拥有相同的心理素质。格雷伯和温格罗[93]写道:“一个以猎象或采摘莲花为生的人,与一个以司机或酒馆老板为生或领导一个大学学科的人一样,可以具有同样的分析、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我们的远古祖先与我们一样,天生并不好战。
那么今天呢?
如果我们拥有在良好的社会中成为好人的潜力,那么为什么这种潜力没有得到发挥呢?
因为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
儿童绝不比成年人低一等。但与成年人相比,他们几乎无法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我们这个充满威权等级制度、剥削、压迫、家庭和国家控制以及环境破坏的世界里,心理健康儿童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
由此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剥夺,以及他们许多需求得不到满足,都会导致悲伤、痛苦和愤怒——而这些情绪通常无法在教育者面前得到充分表达。因此,这些情绪积聚起来,直到达到破坏性的程度——后来,在学校、教育、职业和工作领域受到的羞辱又加剧了这种情绪。由于这种积压的情绪通常不能公开表达——除非成为士兵等——它们被隐藏在社会适应性、礼貌和友善的外表之下。因此,向上卑躬屈膝、向下欺凌他人的「权威性人格」仍然存在。[94]
这对整个社会结构都有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些破坏性的情绪不仅潜藏在内心深处,而且随时可能因某些事件而爆发。如果媒体和政界将社会弱势群体或被妖魔化的「陌生人」作为攻击目标,这种情绪就更容易爆发。在德国,过去这些目标主要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俄罗斯人——目前再次成为目标的是俄罗斯人,不久后可能还会包括中国人。[95]
通过这种方式,即通过大规模地培养破坏性的心理结构并利用媒体进行操纵,人们试图将人们训练成「善战」的人。我们越是被灌输攻击性,越是被破坏自尊,就越容易被用于各种破坏目的——无论这些目的是以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帝国主义、破坏环境、仇视儿童、仇视妇女、仇视同性恋或仇视外国人的意识形态为幌子。
如果大量积压的愤怒得到发泄,人们的思想就会发生转变:恐怖和谋杀可以以「右翼」或「左翼」世界观为借口,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真主的救赎、为了生态独裁,或者像现在这样,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基于规则」的世界幸福计划的一部分。
 心理分析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在 1933 年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中描述了这一基本过程:对儿童的压迫使他们「胆小、怯懦、畏惧权威,在市民意义上表现得乖巧、易于教育」。儿童首先经历「家庭这个权威的微型国家,[…]以便后来能够适应整个社会框架」。在经历了这种教育过程后,积压的生命能量无法通过自然途径得到释放,于是寻找替代出口,流入自然的攻击性,并将其升级为「残酷的虐待狂,成为少数人出于帝国主义利益而策划的战争群体心理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心理扭曲的人会「行动、感受和思考」与自己的生命利益相悖。[96]
心理分析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在 1933 年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中描述了这一基本过程:对儿童的压迫使他们「胆小、怯懦、畏惧权威,在市民意义上表现得乖巧、易于教育」。儿童首先经历「家庭这个权威的微型国家,[…]以便后来能够适应整个社会框架」。在经历了这种教育过程后,积压的生命能量无法通过自然途径得到释放,于是寻找替代出口,流入自然的攻击性,并将其升级为「残酷的虐待狂,成为少数人出于帝国主义利益而策划的战争群体心理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心理扭曲的人会「行动、感受和思考」与自己的生命利益相悖。[96]
就这样,我们被「塑造成」了「战士」。
但由于我们天生就具有和平、团结和亲社会性——没有其他人,我们就无法「像人一样」,在生命的开始阶段也无法存在——因此,被塑造成「善战」的人会让我们感到痛苦。
替代方案、展望
问题仍然存在:为了使人类重新变得像他们出生时那样和平,或者更理想的是,为了使他们能够一直保持和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由于我已经多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97],因此我将非常简短地谈一下。
我们仍然需要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彻底变革,摆脱我们越来越破坏性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但仅此还不够,最终失败的「真实社会主义」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必须进行一场心理社会革命。
威廉·赖希在 1934 年准确指出了其背后的联系:
「如果只试图改变人的结构,社会会产生抵触。如果只试图改变社会,人会产生抵触。这表明,两者不能单独改变。“[98]
对于我们当今时代,这可以具体化为:成年人应该——尤其是利用心理治疗知识——努力克服他们因社会化而形成的心理障碍,同时确保他们的子女和孙辈不会出现这些障碍。

心理分析学家汉斯-约阿希姆·马茨(Hans-Joachim Maaz)在《情感堵塞》(Der Gefühlsstau)[99]等著作中,将相应的「治疗文化」概念引入了东德转型期,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关系文化」[100]。
用爱陪伴孩子成长,积极追求良好、平等的伴侣关系、 追求满足的性生活和心理健康,在家庭、学校、工作、媒体、教会、政治和国家中谴责私下和公开的专制、反生命甚至煽动战争的规范,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抵抗这些规范——这些做法自那时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101]
埃里希·弗洛姆对这种努力的长期目标做了最简洁的描述:一个「健康的社会」,「没有人再感到威胁:孩子不会受到父母的威胁;父母不会受到上级威胁;一个社会阶级不会受到另一个社会阶级的威胁;一个国家不会受到超级大国的威胁」。[102]
***
注释和来源
[1] 本文的早期版本于 2023 年发表在我的网站上,并于 2025 年发表在 apolut 上(https://apolut.net/sind-wir-geborene-krieger/)。本文的修订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史前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马丁·库肯堡(Martin Kuckenburg)的富有成效的交流。
由于本文涉及我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多个科学领域,并且主要使用二次资料,我建议读者参考文中提到的书籍,并随时上网搜索考古发现的最新信息,以形成自己的看法。
[2] https://de.wikipedia.org/wiki/Krieg#Ebenen_der_Kriegsf%C3%BChrung。
[3] 「战争是万物的父亲,万物的国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一些人成为人,一些人成为奴隶,一些人成为自由人」(https://de.wikipedia.org/wiki/Heraklit)。
[4] 「我首先证明,没有文明社会的人类状态(这种状态可称为自然状态)无异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人都有权做任何事情」(https://de.wikipedia.org/wiki/Bellum_omnium_contra_omnes)。
[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0)[1929]:《文化中的不安》,载于:GW 第 14 卷,Fischer,第 419-506 页,此处为第 471 页。关于弗洛伊德在此处错误地引用霍布斯并诋毁狼,参见:https://andreas-peglau-psychoanalyse。 de/der-mensch-ist-dem-menschen-kein-wolf-ueber-eine-eklatante-freudsche-fehlleistung/。
[6] 自 2016 年 5 月以来,奥巴马「正式成为战争天数最多的美国总统」。在他的统治下,美国「总共进行了 2663 天的战争」(https://www.spiegel. de/panorama/krieg-barack-obama-ist-der-us-praesident-mit-den-meisten-kriegstagen-a-00000000-0003-0001-0000-000000567071). 此外,「无人机杀戮成为国家政策,他每周都会签署所谓的『杀戮名单』」(https://www.deutschlandfunkkultur.de/drohnenkrieg-obamas-toedliches-erbe-100.html),数千名无辜者成为「附带损害」的牺牲品。
[8] https://www.zukunftsinstitut.de/artikel/warum-gibt-es-noch-immer-kriege/ 在该研究所新设计的网页上,我无法找到 2025 年 3 月发表的这篇文章。
[9] 同上。
[10] 马丁·库肯堡(Martin Kuckenburg)(1993):《德国史前定居点,公元前 300000 年至公元前 15 年》,杜蒙出版社,第 10 页。
[11] https://de.wikipedia.org/wiki/Menschenaffen#Entwicklungsgeschichte。在 https://de.wikipedia.org/wiki/Hominisation 上提到的是 500 万到 700 万年,而在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tammesgeschichte_des_Menschen 上提到的是 790 万年。根据当今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行为来推断当今人类的心理社会特征是非常推测性的: 在六百万年的独立进化过程中,两种物种都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学家 R. B. Ferguson 对认为当今黑猩猩是「杀人猿」的研究进行了调查,这种说法往往被解释为人类的遗传缺陷。结果表明:在 18 个黑猩猩研究地点「总共 426 年的实地观察」中,记录或推测到的 27 起同种杀戮事件中,“有 15 起来自两个冲突严重的场合[……]。其余 417 年的观察结果表明,平均每年只有 0.03 起杀戮事件。」 此外,弗格森认为,这些致命的冲突「并不是一种进化策略,而是对人类干预黑猩猩栖息地的反应」(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ar-is-not-part-of-human-nature/,翻译:A.P.,参见马丁·库肯堡,1999:《伊甸园在尼安德特人那里吗?《寻找早期人类》,Econ,第 154 页及以下)。
[12]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tammesgeschichte_des_Menschen。
[13] https://www.mpg.de/11820357/mpi_evan_jb_2017。但是:由于「现代人的外貌存在广泛差异」,「对于『现代人』的定义以及他们何时首次出现在化石中,尚无统一意见」(G. J. Sawyer/ Viktor Deak:《人类漫长的进化之路。七百万年的进化历程》,Spektrum 2008,第 174 页)。对于更早的人类前人类,发现的情况越来越不清楚。在许多情况下,年龄相差数十万年的骨骼,或者发现地点相距数千公里的骨骼,被组合在一起,以(重新)构建假定的类人猿物种(同上,例如第 13 页及以下)。例如,备受瞩目的「丹尼索瓦人」除了通过 DNA 分析外,还通过一个指骨(年龄:48000 至 30000 年)、一个脚趾骨(年龄:130000 至 90900 年)、 两颗臼齿(一颗超过 50000 年,另一颗不到 50000 年),所有这些遗骸都在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地区发现,以及在中国西藏出土的一块下颌骨(年龄:160000 年)(https://de。 wikipedia.org/wiki/Denisova-Mensch; https://www.mpg.de/5018113/denisova-genom)。
[14] https://www.planet-wissen.de/natur/energie/feuer/index.html
[15] James C. Scott (2019): Die Mühlen der Zivilisation. 《最早的国家深层历史》,苏尔坎普出版社,第 20 页,参见汉内斯·斯图贝(2021):《世界心理学史》,帕布斯特出版社,第 27 页。
[16] David Graeber/ David Wengrow(2021):《起源。人类的新历史》,克莱特-科塔出版社,第 96、98 页。库肯堡(如注释 11、第 13-15 页)也以非常相似的方式描述了考古学和古人类学面临的障碍。
[17] Harald Meller、Kai Michel、Carel van Schaik(2024):《暴力的进化。为什么我们想要和平,却发动战争》,dtv,第 136 页。
[18] 同上,第 152 页。
[19] https://www.sueddeutsche.de/projekte/artikel/wissen/acht-milliarden-menschheit-wachstum-e418385/ 关于史前人口剧烈波动的假设,参见:https://science.orf.at/stories/3221020/。
[20] 由于随着时间推移,在 3000 具遗骸中发现的骨骼碎片越来越少,因此,如果将范围扩大到智人以外,总数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据称曾生活过的「数百万尼安德特人」中,迄今为止只发现了「两三百具遗骸」(Rebecca Wragg Sykes,2022:《被误解的人类。尼安德特人的生活、爱情与艺术的新视角》,Goldmann,第 63 页)。
[21] Graeber/ Wengrow(如注释 16),第 100 页及以下。经常用于测年的放射性碳测年法也只适用于最近 6 万年:https://de.wikipedia.org/wiki/Radiokarbonmethode。
[22] https://science.orf.at/stories/3219658/
[23] 参见斯图贝(如注释 15),第 15-67 页。
[24] 克里斯托弗·瑞安/卡西尔达·杰塔(2016):《性:真实的故事》,克莱特-科塔出版社,第 223 页。
[2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Cranium-17-bone-traumatic-fractures-A-Frontal-view-of-Cranium-17-showing-the-position_fig4_277326376;https://www.20min。 ch/story/cranium-17-das-aelteste-mordopfer-der-geschichte-162218687169。
[26] 梅勒等人(如注释 17),第 146 页。
[27] 同上,第 139 页。
[28] https://de.wikipedia.org/wiki/Krieg。
[29] 同上。
[30] R. Brian Ferguson,《战争的起源》(https://www.naturalhistorymag.com/htmlsite/0703/0703_feature.html)。翻译:A.P.
[31] https://www.scinexx.de/news/geowissen/kein-steinzeit-krieg-in-jebel-sahaba/。
[32] Dirk Husemann(2005):《人类发明战争的时候》,Thorbecke,第 34 页。
[33] 同注释 31。
[34] Husemann(同注释 32),第 34 页。Meller 等(同注释 17),第 154f 页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35] 同上,第 155 页。
[36] Wragg Sykes(如注释 20),第 25 页。今天,人们似乎已经普遍认为,智人灭绝了尼安德特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参见同上,第 451-454 页;马丁·库肯堡(Martin Kuckenburg)(2005):《尼安德特人。Auf den Spuren des ersten Europäers(《追寻第一位欧洲人的足迹》),克莱特-科塔出版社,第 282-296 页;梅勒等人(如注释 17),第 142 页。
[37] 梅勒等人(如注释 17),第 146 页及以下、第 162 页。
[38] 35000 年前,地球上最多只有 300 万人(Scott,如注释 15,第 22 页)。
[39] Ryan 和 Jethá(如注释 24,第 201 页)称其为「原始丰裕社会」。这是参考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gs)的论文《原始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https://www.uvm.edu/~jdericks/EE/Sahlins-Original_Affluent_Society.pdf(另见:https://www.matthes-seitz-berlin.de/buch/die-urspruengliche-wohlstandsgesellschaft.html)。當然,當時也存在氣候變化,例如導致冰河時期。但通常情況下,這種變化非常緩慢,人們可以適應(Wragg Sykes,見註釋 20,第 104-124 頁)。认为 70,000 多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导致几乎整个人类在短时间内灭绝的说法存在很大争议(https://de.wikipedia.org/wiki/Toba-Katastrophentheorie)。
[40] Rutger Bregman(2020):《本质上是好的。人类的新历史》,Rowohlt,第 115 页。已知最古老的洞穴壁画已有 45000 年的历史(https://de.wikipedia.org/wiki/H%C3%B6hlenmalerei)。
[41] https://de.wikipedia.org/wiki/Massaker_von_Kilianst%C3%A4dten、https://de.wikipedia.org/wiki/Massaker_von_Halberstadt、https://de.wikipedia.org/wiki/Massaker_von_Talheim、https://de。 wikipedia.org/wiki/Massaker_von_Schletz;https://www.scinexx.de/news/archaeologie/war-dies-der-erste-krieg-europas/。
[42] https://de.wikipedia.org/wiki/Felsmalereien_in_der_spanischen_Levante。另见胡斯曼(如注释 32),第 61 页及以下。
[43] 最早使用武器狩猎的证据可追溯到大约 50 万年前(https://www.spiegel.de/wissenschaft/mensch/fruehmenschen-jagten-schon-vor-500000-jahren-mit-stein-speerspitzen-a-867412.html)。只有 30 万年前的矛才能被「确凿地认定」为狩猎武器,这些矛是在下萨克森州的舍宁根发现的,与许多被杀死的野马的骨头一起埋在地下(Martin Kuckenburg,202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早期历史与现代考古学》,无出版地,第 79 页)。但是,能够用它们来猎杀动物并不意味着人们想用它们来杀戮人类。2025 年,采用一种有争议的测年方法后,这些矛的年龄被估计为只有 20 万年(https://www.welt.de/wissenschaft/article256093064/Archaeologie-Die-Schoeninger-Speere-sind-100-000-Jahre-juenger-mit-Folgen.html)。
[44] 参见斯科特(如注释 15),第 159-164 页。
[45] Brigitte Röder/ Juliane Hummel/ Brigitta Kunz(2001)[1996]:《女神的黄昏。从考古学角度看母系社会》,Königsfurt,第 396 页。另见 Graeber/ Wengrow(如注释 16),第 238-244 页。
[46] Scott(如注释 15),第 20 页。另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Geschichte_der_Schrift。详细信息:Martin Kuckenburg(2016):《谁说了第一个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Theiss。
[47] Bregman(如注释 40),第 139-161 页。
[48] Kuckenburg(如注释 36),第 9 页。
[49] https://de.wikipedia.org/wiki/Neandertaler#Verwandtschaft_zum_modernen_Menschen。
[50] Stubbe(如注释 15),第 33 页。
[51]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比我们更聪明,但有可能(参见同上,第 25 页)。
[52] 参见注释 16 和 36 等。
[53] R. Brian Ferguson(2013): 《平克名单:夸大史前战争死亡率》,载于道格拉斯·P·弗莱(Douglas P. Fry)编辑的《战争、和平与人类本性》(War, Peace, and Human N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12-131 页(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3371719_Pinker’s_List_Exaggerating_Prehistoric_War_Mortality)。另见瑞安/杰萨(如注释 24),第 212-215 页和布雷格曼(如注释 40),第 112 页及以下。
[54] 梅勒等人(如注释 17),第 37 页。
[55] https://scilogs.spektrum.de/menschen-bilder/wird-alles-immer-besser-ein-kritischer-blick-auf-steven-pinkers-geschichtsoptimismus/。
[56] https://de.wikipedia.org/wiki/Napoleon_Chagnon。
[57] Ryan/ Jethá(如注释 24),第 223-227 页;Bregman(如注释 40),第 111f 页。
[58] Bregman(如注释 40)。
[59] 在人类学中,由于缺乏可评估的史前遗迹,人们往往根据最近几千年的传说或对狩猎采集者的实地观察来推断早期智人的生活方式。但这些也只是猜测。尤其是今天,几乎不再存在与世隔绝的民族。参见马丁·库肯堡(Martin Kuckenburg)(202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早期历史与现代考古学》,无出版地,第 136 页及以下。
[60] https://de.wikipedia.org/wiki/Thomas_Hobbes。
[61] 梅勒等人(如注释 17),第 113 页。
[62] 瑞安/杰萨(如注释 24),第 204、236、238 页。
[63] 梅勒等人(如注释 17),第 113 页。
[65] 同上,第 272 页。翻译:A.P.
[66]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taatsentstehung。
[67] Scott(如注释 15),另见 https://www.soziopolis.de/die-muehlen-der-zivilisation-1.html。
[68] https://de.wikipedia.org/wiki/%C3%87atalh%C3%B6y%C3%BCk。
[69] Graeber/ Wengrow(如注释 16),第 236、245 页及以下。
[70] https://www.uncg.edu/employees/douglas-fry/。
[71] https://sustainingpeaceproject.com/。
[72] https://greatergood.berkeley.edu/article/item/what_can_we_learn_from_the_worlds_most_peaceful_societies。翻译:A.P.
[73] 同上。
[74] 道格拉斯·P·弗莱(2005):《人类对和平的潜力:对战争与暴力的假设的人类学挑战》,牛津大学出版社;https://sustainingpeaceproject.com/。
[75] 埃里希·弗洛姆(1989):《人类破坏性的解剖学》,同上:全集,第 7 卷,dtv
[76] 同上,第 148-262 页。1998 年,民族志地图集还记录了 160 个「纯母系」——即只考虑母亲血统的「土著民族和族群」。这至少占全球记录的 1267 个族群的 13%(https://de.wikipedia.org/wiki/Matriarchat)。
[77] Fromm(如注释 75),第 158 页及以下。
[78] 更多相关内容:https://andreas-peglau-psychoanalyse.de/wp-content/uploads/2018/07/Mythos-Todestrieb-pid_2018_02_Peglau.pdf。
[79] 我的治疗工作也不断证明,人们能够克服破坏性的影响,这是完全可能的。
[80] 参见戈培尔,约瑟夫(1992) [1990]:《1924-1945 年日记》五卷本,雷乌特,拉尔夫·乔治编,Piper 出版;朗格里希,彼得(2010):《戈培尔》。传记,西德勒;鲁特,拉尔夫·G.(1991)[1990]:《戈培尔》,皮珀,其中以下内容参见第 11-75 页。
[81] 同上,第 52 页。
[82] 同上,第 47 页。
[83] 同上,第 52 页。
[84] 同上,第 68-73 页。
[85] 同上,第 63 页。
[86] 同上,第 73 页。
[87] Longerich(如注释 80),第 58 页。
[88] Reuth(如注释 80),第 104 页。
[89] Hannes Leidinger/ Christian Rapp(2020):《希特勒——塑造他的岁月。童年与青年 1889-1914》,Residenz。另见:Brigitte Hamann(1998):《希特勒的维也纳:一个独裁者的学徒岁月》,Piper。
[90] 同上,第 152 页。详细信息:Brigitte Hamann(2010):《希特勒的贵族犹太人:穷医生爱德华·布洛赫的一生》,Piper。
[91] Meller 等(如注释 17),第 124 页。
[92] 除本文中使用的书籍外,另见杰拉尔德·许特(2003)[1999]:《爱的进化。达尔文已经预见到,但达尔文主义者却不愿承认的事实》,范登霍克/鲁普雷希特出版社;马克·索尔姆斯/奥利弗·特恩布尔(2004):《大脑与内心世界。神经科学与心理分析》,Walter,第 138 页及以下,第 148 页;Michael Tomasello(2010):《我们为什么合作》,Suhrkamp;Stefan Klein(2011)[2010]:《给予的意义。为什么无私在进化中占上风,而自私无法让我们前进,Fischer;约阿希姆·鲍尔(Joachim Bauer)(2015):自我控制。自由意志的重新发现,Blessing。埃尔温·瓦根霍夫(Erwin Wagenhofer)于 2013 年发布的纪录片《字母表——恐惧还是爱》也以动人的方式说明了这一点(http://www.alphabet-film.com/)。
[93] 同注释 16,第 114 页及以下。另见布雷格曼(如注释 40),第 79 页及以下。
[94] 参见:https://duepublico2.uni-due.de/servlets/MCRFileNodeServlet/duepublico_derivate_00045266/05_Peglau_Autoritarismus.pdf。
[95] 另见 https://andreas-peglau-psychoanalyse.de/andreas-peglau-utopie-oder-dystopie-zitate-und-notizen-zu-china-mai-2020-bis-oktober-2021/。
[96] 威廉·赖希(2020):《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原文,Psychosozial,第 38、40 页。
[97] 例如在安德烈亚斯·佩格劳(2024):《人作为傀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学说中如何压制了真实的心理(https://andreas-peglau-psychoanalyse.de/menschen-als-marionetten-wie-marx-und-engels-die-reale-psyche-in-ihrer-lehre-verdraengten/),第 70-74 页,或参见: https://www.manova.news/artikel/rechtsruck-in-deutschland。
[98] 威廉·赖希(同注释 96),第 195 页。
[99] 另见:https://andreas-peglau-psychoanalyse.de/psychische-revolution-und-therapeutische-kultur-vorschlaege-fuer-ein-alternatives-leben/。
[100] 参见:https://hans-joachim-maaz-stiftung.de/hans-joachim-maaz/buecher-von-hans-joachim-maaz/。
[101] 另见 https://apolut.net/im-gespraech-andreas-peglau/。
[102] 埃里希·弗洛姆(同注释 75),第 395 页。
互联网资源最后查询时间:2025 年 5 月 14 日
请引用为
安德烈亚斯·佩格劳(2025):我们不是天生的战士。关于和平与「战争能力」的心理社会前提(https://andreas-peglau-psychoanalyse.de/wir-sind-keine-geborenen-krieger-zu-psychosozialen-voraussetzungen-von-friedfertigkeit-und-kriegstuechtigkeit/) Chinesische Übersetzung.
欢迎将本文用于非商业目的进行转载和传播。
根据知识共享许可(署名 – 非商业性 – 禁止修改 4.0 国际,CC BY-NC-ND 4.0)